1957年秋,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和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邯郸西郊的涧沟村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在两个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灰坑中,分别放置了三个人头盖骨(1)。两个灰坑都略呈圆形,甚浅,底部稍平,其中一个还有进出的台阶,原先可能是一种半地穴式的窝棚建筑。人头盖骨就在窝棚底部的中间部位,发现时已部分地为后期钙质所遮盖。清除钙质层,就清楚地显露出斧子砍过的伤痕和剥头皮时留下的刀痕。兹将各个标本的情况分述如下:
1、编号T39⑥B∶2,头骨完整,骨质很薄,额部较高而光,骨缝尚未完全密合,可能是一个青年女性的。断口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砍下来的。边缘不甚整齐,看来所用的斧子并不锋利(图版拾壹,3)。在枕尖下偏左方有横向的斧痕八条,每条痕迹长3—6毫米,大多呈楔形,当是砍头时因偏离了位置而留下来的。在头盖骨的正中部位,从额部经头顶直至枕部有一道很直的刀割痕迹,较浅而宽,并有来回错动的现象,当是剥头皮时遗留下来的。看来所用的刀子也不锐利,很像是石刀所为(图版拾壹,1)。
2、编号T39⑥B∶3,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厚薄中等,可能也是一个青年女性的。断口系用斧子砍成。枕骨上遗留斧痕二十余条,方向从右上至左下,长短和深浅颇不一致,有的略呈楔形,楔端宽2—5毫米,长5—20毫米,当是由不甚锋利的斧子砍成(图版拾壹,2)。从斧痕的方向推测,应是在死者扑倒在地时砍下来的。顶骨中央从前到后有大量来回错动的细刀痕,其中有两条一直延伸到额部,向后隔了一段,到枕骨上方又有同方向的刀痕十条。这些刀痕显然也是剥头皮时遗留下来的。
3、编号T39⑥B∶9,仅剩下头骨左侧一块,厚薄中等。上方有一条斧子痕迹,左方(即前方)有六条斧子痕迹,均宽而浅,长5—15毫米不等。右方(即后方)有密集的刀割痕迹十余道,很细很短,长仅5毫米,也应是一种割头皮的痕迹。
4、编号H13∶3(原号T18④B∶3),仅有顶骨及枕骨,缺少额部。骨壁较厚。顶骨近额处有楔形斧痕四条,长10毫米,楔根宽2.5毫米,楔尖朝后偏右,当是将死者踩在地上并从右后方砍下来的。
5、编号H13∶7,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较厚,可能属男性。断口是用斧子砍下来的,边缘不太整齐。额部偏右有两条斧痕,正前后方向,长6毫米(图版拾壹,4)。
6、编号H13∶120,骨壁特厚,全部密合无接缝,像是一个男性的完整头盖骨。也是用斧子砍下来的,边缘不整齐,额部遗留一道斧子痕迹,呈楔形,尖端朝上。
综观上述六个标本,有一些颇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从斧痕的方向和部位来看,当是在被砍者扑倒在地,甚至被他人踩在脚下时砍去头盖的。砍时有的人可能还在挣扎,因而个别的斧痕砍偏了,有的甚至砍到头顶上去了。如果是拿着骷髅来砍,就不会出现这些现象。
第二,刀痕和斧痕大都较浅而宽,显然并不十分锋利。看来所用的武器都是石器而没有用金属兵器。
第三,两个窝棚中放置的头盖骨都是两整一残,而且一边是男性,另一边是女性。当然,因为仅剩头盖,性别的鉴定容有不甚准确之处,但两组有明显的差别,则是一个事实。这究竟是有意识的安排,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呢?
第四,从头盖骨的长势来看,都应是青年或中年,而没有老人和小孩,并且女性的年岁较男性更小一些。
第五,从剥头皮的痕迹来看,只有在女性头盖骨上看得明显,男性的则没有。或者说一个窝棚中的头盖有,另一个窝棚中的没有。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只有女子才剥头皮,男子的不剥,仅仅做成头盖杯。另一种可能性是两性的剥头皮方式不同;女性把头皮从中切开,向两边剥;男性把头盖砍下后,揪着头皮整个儿地剥下来,因而可以不留下任何刀痕。
这一发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全面地评价它的意义在现时也还是很困难的。有些同志推测这些头盖骨是猎头的标本,但从民族学的角度考察,猎头的风俗主要是在南方流行。例如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许多民族都曾有过猎头风俗,我国云南的佤族也曾有过这种风俗,而北方各族是没有的。况且猎头都是齐颈部砍下来的,所得标本应该是整个的人头而不仅仅是一个头盖骨,通常也不剥去头皮。所以涧沟的头盖骨应与猎头风俗无关。
明斯在其所著《斯基太人与希腊人》一书中,曾经发表了一件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出土的头盖骨标本(2),也是齐眉弓经耳际到枕骨砍下来的,断口颇不整齐,其形状和做法都和涧沟的头盖骨基本相同。作者认为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头盖杯,看来涧沟的头盖骨标本也应当是一种作为饮器的头盖杯。
历史上流行头盖杯风俗的主要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诸如斯基太人、匈奴、蠕蠕、伯子勒克和党项等都是,西藏、乌浒、古宗等也有这种习惯,《史记·大宛列传》中大月氏条记载:“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汉书》卷九六上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里所谓以其头者,当然是以其头盖骨,否则是不好做饮器的。至于斯基太人,古代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经相当详细地记述了他们的风俗,对于我们了解制做头盖杯的动机、方法和头盖杯本身的功用很有帮助。他在有名的巨著《历史》第四卷第六十五节写道:
斯基太人“只是对自己最痛恨的敌人才这样作:每个人都把首级齐眉毛以下的各部分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就使用;如果他是一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贴上金箔,再把它当作杯子来用。有的人也用本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杯子,但那人必须是同他不和,并且被他在国王面前打败过的。如果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问时,他便用这些头盖杯来款待。并且告诉客人,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曾经怎样地向他挑战而又被他打败,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勇武。”
涧沟头盖杯所属的时期大体相当于龙山文化的较早时期,距离现在有四千三百年,估计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王,但至少应有部落联盟的军事酋长。我们在同一遗址同一时期的遗存中,还发现一个灰坑里杂乱地扔置十具人骨,其中有的作挣扎的姿态,有的头部有击伤的痕迹,另有一个水井废弃后也扔进去了许多死者,骨骼迭压达五层之多,而且相当零乱。这种情况在龙山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当是社会进入军事民主时期之后,部落间经常发生掠夺性战争的一种反映。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某些特别英勇的战士是有可能把敌人的头盖揭下来做饮器的。涧沟头盖骨所代表的个体全系中年和青年男女这一事实,也许正好说明他(她)们自己生前就是战士,只不过最后被打败了,才落得了这般厄运。
涧沟所在的位置属于历史上中原地区的范围,历来是华夏民族活动的重要历史舞台,由于这批头盖杯的发现,可知古代的华夏民族也有此种风俗习惯。不但如此,在龙山时代后的商周时代,仍然不时有做头盖杯的事例,因而对于华夏民族来说,涧沟的发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风俗传统的开始。
就我们所知,商代前期继续存在着做头盖杯的风俗。1973年,当河南省博物馆的同志们在郑州商城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其东北部发现了大片宫殿基址和濠沟等。其中有一条近南北向的濠沟就堆集了近百个人头盖骨,有八十多个层层迭压成两大堆。一般是从眉弓和耳际的上端横截锯开的,断口比较整齐,不少标本上还留有明显的锯切痕迹(3)。这是在我国发现头盖杯最多的一次。在此以前,曾在商城以北的一处制骨作坊中发现一个窖穴,出土许多骨镞、骨簪及其半成品和骨料等,总数达一千多件,大多用人的肢骨或肋骨制成(4)。可见商代用人骨做器具并非偶然事例,它既是奴隶制时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斗争的产物,也当是从龙山时代开始的头盖杯风俗的一个发展。
到商代晚期,虽然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头盖杯,但刻着文字的人头骨碎片则不止发现一起。其中有的刻着“□□伐人方白(伯)”,有的刻着“……方白(伯),用……”(5)。它们很可能是商王朝向各方国举行征伐时,砍下敌人的首级做头盖杯,并在其上刻辞以志战功的遗物。只是现在已成碎片,看不出原来器物的模样了。
华夏民族做头盖杯的风俗直到战国初年还见于记载。《战国策·赵策一》写到:“及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这正如斯基太人将其“最痛恨的敌人”的首级取下来做饮器是一样的。
头盖杯风俗虽然曾经在许多民族中流行,但从分布的范围来看毕竟只限于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地区,而且彼此之间是相互邻接的。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各族的头盖杯风俗也许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甚至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白鸟清吉认为,这种风俗是以西藏为中心发源地而向东西两方面传播开来的(6)。但西藏做头盖杯的历史比其它地方要晚,直到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的农奴主不但用人头做杯子,而且还有把人皮剥下来晒干,或把手脚砍下来腊制的。那是某些残酷的农奴主对敢于反抗或逃亡的农奴的一种惩罚行为,同匈奴人和斯基太人等主要表现为民族斗争和尚武精神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白鸟清吉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如果就时间的先后来排比,涧沟的头盖杯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标本。不妨认为古代的华夏是首先流行这种风俗的民族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起源中心的话。
至于剥头皮的风俗,世界上最盛行的莫过于美洲印第安人。例如北美东部的易洛魁人和马斯科基人在作战时,总是设法用尖刀割取敌人不大的一块带发头皮,晒干以后加上装饰并保存起来。一个战士拥有敌人头皮的多少,乃是他的英勇程度和军事功绩的重要标志(7)。但这类关于印第安人剥取头皮的记录都是近代的事,究竟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种风俗不得而知。至于斯基太人的剥头皮风俗,则同他们的头盖杯一样古老。希罗多德在前引同一著作的第六十四节写道:
“斯基太人喝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人的血。并把他杀死的所有人的首级带到国王那里去……他齐着耳朵在头上割一圈,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随后再用牛肋骨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用它当作手巾,吊在自己所骑的马的马勒上以示夸耀;凡是拥有用头皮制成的手巾最多的人,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
斯基太人和印第安人地理悬隔,时代相差很远,社会发展阶段也不相同,两者的风俗自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例如剥头皮的方法就不相同,一个是剥取不大的一块带发头皮,一个是把整张头皮剥下来做为手巾。但奇怪的是二者的动机和效用基本相同,都是要剥取敌人的头皮做成纪念品,都是作为战士英勇顽强的标志,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它地区剥头皮风俗的意义。
关于古代剥头皮的实物标本,首先是在阿尔太地区的巴泽雷克发现的。当四十年代末期,苏联的考古学家曾经在那里发掘了一系列巨大的古冢,其中第二号冢墓埋葬了一位年约六十岁的男性老人,尸体因在永冻层中而被长期保存下来,体质特征属蒙古大人种。他的头部有三处用斧子砍伤的痕迹,头皮也被剥去了,换上了一块假头皮,那是用马鬃将牦牛皮缝上去的(8)。推测他是一位在战场上不幸丧命的首领,因被敌人剥去了头皮,族人夺回他的尸体之后,只好补上假头皮而安葬。该墓的年代约当公元前三至二世纪,正值斯基太人发展的晚期阶段,其随葬器物有不少具有浓厚的斯基太作风,看来其剥头皮风俗也可能是在斯基太人的影响下发生的。
从头盖骨上的痕迹来看,涧沟的剥头皮方法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强调性别的差异:女性的从头顶剖开,将头皮一分为二,这样比较容易剥取下来;男性头盖骨上因未发现刀割痕迹,也许根本就不剥头皮,也许是像斯基太人那样齐断口摇取整张头皮,不论属于何者,总之对两性的处置方法是有差异的,这与斯基太人和印第安人等都不相同。
世界上具有剥头皮风俗的民族也是很多的。根据江上波夫的研究,除上面提到的斯基太人、美洲印第安人和巴泽雷克古冢所属的居民外,还有埃兰、回鹘、俄斯恰克和鲜卑等(9),他们多是北方游牧民族。不过从总的分布范围看,与头盖杯风俗并不一致。两种风俗兼而有之的,斯基太人有一例,涧沟的发现是第二例,可见这两种风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剥头皮风俗流行的年代,各地区间是参差不齐的,其中还是以涧沟为最早。如果探索这种风俗的起源,不论其结果是多元的还是单元的,涧沟的资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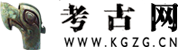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