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杂剧五色砖雕
去年底,在整理馆藏文物时,我们发现了一批含有金大定七年(1167年)杂剧五色砖雕的文物,计有砖质买地券一方(图一,高32.5;宽32.5;厚5 厘米),砖质画像四方:韩氏“阿郎阿娘”铭文画像(图二,高32.5 宽32.5厚5 厘米),韩氏“二叔二母”铭文画像(图三,高32.5 宽;32.5 厚;5 厘米),韩氏“三叔三母”铭文画像(图四,高32.5;宽32.5;厚5 厘米),韩氏“六叔六母”铭文画像(图五,高32.5;宽32.5;厚5 厘米),平剔线刻杂剧砖雕五方(图六,各高30;宽15;厚5 厘米) 等六种十件。通过排比分析,我们感到这组有明确纪年的属于金代(1115 年-1234 年) 初期的杂剧五色砖雕,不仅在黄河南岸(洛阳市) 属于首次发现,意义重大[属于黄河南岸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金代杂剧文物,据车文明先生《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统计,只有属于金代末期的义马市南郊金贞祐四年(1216)墓的四方杂剧砖雕] ,而且在认识中国戏曲形态成熟年代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这组金世宗大定七年的杂剧五色砖雕,与山西芮城永乐宫潘德冲墓石棺元杂剧线刻图、山西稷山店头村元代杂剧砖雕、山西新绛寨里村元杂剧砖雕进行比较,发现不论其角色类型和人数,还是其服饰和砌末,都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再将其与山西稷山化峪2 号、3 号金墓杂剧砖雕、山西侯马董明墓金代杂剧砖雕、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传出山西侯马金墓杂剧五色砖雕(图七)进行比较,发现不论其角色类型和人数,还是其服饰和砌末,也同样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再将其与河南偃师酒流沟水库宋墓杂剧砖雕、河南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杂剧砖雕、河南温县博物馆藏宋杂剧砖雕、河南洛阳关林庙宋墓杂剧砖雕(图八,《洛阳洛龙区关林庙宋代砖雕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8 期,第109 页),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传出河南温县宋墓的两组杂剧砖雕(图九、图十,见廖奔、赵建新《中国戏曲文物图谱》,中国戏剧出版社,第201 页)进行比较,发现不论其角色类型和人数,还是其服饰和砌末,也照样都是高度一致的。
关于宋、金、元杂剧音乐伴奏之乐器种类和脸部化妆方面的高度一致性或者说连续性的例证,刘念兹先生在《金元杂剧在平阳地区发展考略》(《中华戏曲》第4 辑)中,有过很具体的论述,此不赘述。
那么,这种始于北宋,历金至元,长达四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杂剧在角色类型和人数、服饰和砌末,以及伴奏乐器之种类和脸部化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度一致性或者说连续性,能够否说明中国戏曲的成熟年代问题?
中国戏曲的成熟年代
元杂剧为中国戏曲之成熟形态,这是自王国维以来学界的共识。但通过对这组戏曲砖雕的对比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反推出北宋杂剧,至少说北宋后期的杂剧,为中国戏曲的成熟形态来呢?
当然,在自北宋历金至元的四百年间,杂剧还是有不少发展变化的。譬如在角色人数上对四或五人的突破,如山西新绛吴岭庄卫家墓元代杂剧砖雕为九人(七方砖雕左右两侧之四人中,两个腰鼓色属于音乐伴奏,其杂剧色实为七个)。但其人数虽然增加到了七个,而其角色类型(末泥、引戏、副末、副净、装孤) 却并未增加,只不过是根据剧情需要增加了两个同类型的演员而已,并不意味着其类型化的角色设置发生了根本变化。
对此,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宋金八人作场的新例证(图十一)。这两方现藏于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砖雕,一方中的四色,同样属于杂剧作场时的音乐伴奏,另一方中的角色类型,也同样只有装孤、引戏或末泥、副末或副净几种,在角色类型上也并未有任何突破。
当然, 在北宋杂剧五色排列顺序中,副末、副净两色往往处于中间位置,这说明滑稽调笑的份量,在当时是占据着杂剧演出的重要位置的。但到金代则出现了末泥和装孤处于中间位置的情况,这说明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在杂剧中的份量,已逐渐加重,但其角色类型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的事实,却同样是没法改变的。
当然,元杂剧作为中国古代戏曲的成熟形态,有一批知名剧作家出现,有大批“大戏”剧本产生,是其重要标志,而宋金时期的“知名”剧作家和“大戏”剧本,则没有被发现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不存在。因为在很多史料文献中都留下了线索,如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撰杂剧本子”的记载;《宋会要辑稿·乐五·教坊乐》:“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的记载;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的284 个“官本杂剧段数”;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的690 个“院本名目”等,以及当时的各种“书会”组织与其中的专门人员“才人”,都表明当时戏曲的兴盛。
而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情节连续的《目连经救母》曾连演七天。从敦煌出土唐本《目连救母变文》的故事情节已经相当复杂的情况来看,宋代目连救母杂剧连演七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即使是剧本长度只够演一天的《目连经救母》,与元杂剧一般长度相比,完全可被视为“大戏”。
再让我们看看北宋民间傩戏发达完善的程度吧——据车文明先生《20 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第65 页讲:20 世纪80 年代发现于山西曲沃任庄的清末抄本《扇鼓神谱》,被认为是一种产生于北宋并保存了许多原始形态的民间傩祭礼仪写本。其中泛戏剧表演剧目《坐后土》被称为北宋傩戏。此剧之基本情节是,后土娘娘千秋华诞之日,令侍者王成告知其五个儿子前来祝贺。占有春夏秋冬的四个儿子奉命前来,第五子因无“江山日期”不肯前来。后土娘娘知情后,从四个儿子所管四季中的每一季末尾各划出18 天,共72 天,名之曰“土王日”,给五子掌管,问题得以解决。剧中上场人物有名目者共七个,全部为神灵,故推测均戴面具。全剧有说有唱,有人物,有情节,并且还有了“暗场”处理与简单的虚拟手法。从《坐后土》这种演出可看出这已是戏曲的成熟状态了。
如果这种民间傩戏可被看作成熟的戏曲形态,那其他非傩戏性质的民间或宫廷杂剧存在成熟的戏曲形态演出,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其实这一观点,早在1977 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伊维德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奚如谷就明确提出:杂剧的分期不应该基于政治事件的历史划分;杂剧和南戏可能早在元代建立之前就已经作为完全成熟的戏剧形态存在了。他们把中国杂剧从发生到衰落的整个时期定在12 世纪到15 世纪中叶——我们则称其为“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学界普遍将元杂剧的称为“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我们是不愿苟同的)。
根据考古发现,结合《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文献中的史料,奚如谷认为:复杂的戏剧表演在北宋时期已经存在,宋金时期已经有严肃的戏剧演出。他还认为:中国最早的戏剧是一种话剧,是活跃在北宋舞台上的通俗民间话剧。其所谓话剧,是指《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和《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中所载“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中的“正杂剧”。结合文献、文物以及杜善夫、高安道的散曲进行比较之后,他认为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杂剧的演出形态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河南偃师酒流沟北宋墓出土的杂剧砖雕,是对他观点最有力的支持。他指出,这些砖雕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砖雕上化妆的演员正在上演一出相当复杂的戏,而这种戏比元杂剧要早一百多年。
尤其重要的是,把北宋的杂剧砖雕同山西永乐宫元初的宋德方墓石棺前壁上的雕刻(此时恰值元杂剧兴盛期)相比较,在服饰化妆和表演动作上都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这两种出土文物的相似性表明,从北宋到元代的戏剧装扮和表演确实保持着连续性,这些证据表明,就戏曲一词的基本意义而言,即由演员身穿剧中角色的服装,以对道白与歌舞表演故事,面对观众在舞台上演出,中国戏曲在元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形成了。鉴于文物、文献与文本材料所揭示的杂剧演出形态的高度连续性,奚如谷倾向于把这种连续性上推到北宋时期。戏曲艺人,无论是随宋室南迁还是继续留在北方,都主要是利用北宋的传统形式来满足观众的要求。那么,既然北宋戏剧和元代戏剧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或者说连续性,宋杂剧自然应该是成熟戏曲形态了。
其实,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的话,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说:“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然宋金演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而其本则无一存,故当日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在这里,先生采取谨慎态度来论说中国戏曲成熟之年代,皆因时代局限而未能看到其后大批出土的宋元戏曲文物所致。
附录:金大定七年《韩□父母墓买地券》文
维大金大定七年①岁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初四日丙午立。子韩□奉为父母□殁故,黾筮叶从,相地袭吉,宜于嵩州②福昌县福庆乡③安厝宅兆,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等地一段,自方一十七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分壁掌四域。丘丞墓伯,封步累畔,道路将军,齐整阡陌,千秋万载,永无殃咎。若辄干犯诃禁者,将军亭长,收付河伯。今以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分付。工匠修营安厝,以后永保休吉。知见人岁月主,保人今日直符,故气邪精不得忏怪。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祸。主人内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
① 大定七年: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七年,公元1167 年。
②嵩州:金置。初名顺州,治伊阳县(今嵩县)。金天德三年(1151 年)改名,辖境约当今河南省嵩县、洛宁和宜阳县西部地。属南京路。
③福昌县:今洛阳市宜阳县,在历史上曾名福昌县、寿安县、福庆县。据《宜阳县志》记载,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更宜阳县为福昌县,以福昌为治所。五代后唐时期(923~936),改福昌县为福庆县。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任福昌县主簿。宋神宗熙宁五年,福昌并入寿安县。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22日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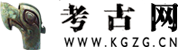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