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Basic Direction of Heritage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 and Culture
【作者简介】王刃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王刃余(1978~),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关 键 词】调查/功能/结构/遗产本体/遗产背景/遗产生境
investigation/functions/structures/heritage/background/ecology
文化遗产调查的内容和应当追问的问题对于遗产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对于文化遗产本身的景观分布范围、社会原生背景、使用和改用状况以及对于反映人地关系和遗产压力等方面因素进行的分析,都是对遗产进行评估和处理的依据来源,这些调查内容都应被视为对遗址进行管理的基本参数来源,也是对遗址进行规划的基础。我国目前的遗产实践中尚存在遗产调查上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遗产调查简单化和离散化,对于遗产调查的细化和整合是亟需解决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对于遗产范围的认定、遗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遗产本身的背景和现实处境都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调查手段。这些问题成为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较大的障碍,而解决的途径应当是改进遗产调查模式。
文化遗产保护
The basic enquiries should be included into a heritage investigation,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authentic geographic landscape and social context in which heritage site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used, adapted, the component indicators of a single heritage site or landscape indicating the ways of human-landscape interactions, the social dimensions in which heritage pressures or impacts can be understood and assessed. All these enquiries should be viewed as the basis for heritage management. Many aspects in Chinese heritage practices need to be improved. Amongst these, the improvement of investigation methodologies comprises the core, especially in zoning, the links between heritage and modern communiti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like. All these elements should be carefully examined before any management plan is produced.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化遗产研究从整体上讲是具有保护性和策略性的研究;从其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属性上讲,这种研究本身应该以构建被保护实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为根本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须要为被认定为一定社会背景中的“遗产”提供处理依据,这就是进行遗产调查的全部动因。简言之,对于遗产的“处理”与对其的“认定”同样需要充足的依据。本文希望能够对遗产调查的基本方向进行如下的讨论。
一 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遗产本体”、“遗产背景”和“遗产生境”
1.文化遗产调查的必要性
文化遗产的行业有着较为杂糅的构成特征,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思路非常复杂,从文化遗产研究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始终处于一个以保护为要务的学科态势。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遗产研究中对于遗产“价值”、“原真性”以及“整体性”的关注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种以上述三个基础概念为基石的遗产调查、认定、评估、列选与保护的系列“研究—管理”模式[1]。“保护科学与技术”(conservation sciences and techniques)是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应用学科,现在它的功能根据不同的保护对象越来越被细化。目前,在我国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将“修复”(restoration)、复建(reconstruction)和“保护科学”结合的过渡阶段。自20世纪后期始,中国“文物”界,除了重视文物保护外,另一发展就是对于区域规划整体思路的看重,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文物法规政策的制定方面以及规划保护方案的制定方面。但20世纪后半期,我国主要的文化遗产实践可以说就是以“文物实体”的保护和复原等具体处理为主所进行的实践操作。而相比之下,遗产的地域规划和整体性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旧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与世界的普遍状况相同[2],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大城市建设和乡村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剧,土地使用方式的变化以及地貌变迁构成了遗产损失的主要成因,对古代遗址与文化景观的处理在21世纪仍旧是工作重心,如何“节度”地表空间与解决实体“保存”的问题是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压力。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3],最主要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一套与遗产地域状况相适应的从调查分析到规划保护与管理的细密体系。从参与遗产行为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该体系往往包括四个方面,即政策制定者、信息搜集与整理者、信息刊布者以及相关社群,这几个相关群体在遗产活动中担负不同的责任。而作为考古遗址和景观的管理,本质上是将遗产对象的相关信息和价值进行收集和有效的利用,将不同的遗址或景观信息传递给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4],从而在决策、保护实践以及公益使用上确保遗址价值的真实与完整。欲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需要对遗产对象的各项信息做细致的分类并形成缜密的调查技术路线。
2.遗产调查构成的三个基本方面
我们无法脱离遗产对象的背景材料而对其进行认识。在这里我们使用“遗产本体”、“遗产背景”以及“遗产生境”三个不同的范畴来廓清文化遗产对象在不同时期的相关背景中存在的含义。“遗产本体”指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实体或者景观,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化资源或者考古资源,而是指物质遗存“存在”和“留存”的基本方式和原因。“遗产背景”指的是在围绕主体存在的过去的环境与社会因素的遗存,这种遗存本身密切关乎主体的实体遗留,特别是反映遗产行为的宗教和社会信仰因素等。而所谓“遗产生境”则是指遗产对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存在的基本方式和所面临的压力。与上面三个层次相对应,调查方法基本包括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即:文化遗产对象实体分布区域的认定和遗产构成要素分析,目的在于确定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遗产背景信息搜集与还原;遗产与现代社会关系(遗产对象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对于一定地域内的遗产对象进行有机地梳理,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多学科合作的遗产调查模式,最终形成具有多重参考价值的地域-遗产档案。
3.遗产对象的确认与景观考古学调查
对于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和遗产类别的划分一直影响着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实践的效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现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的扩张。从最早的“文化财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考古和历史遗址”、“单体建筑”、“建筑群”、“城乡建筑区域”、“历史区域”、“民族建筑”及其“周边环景”(setting),发展到后来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文化城镇与城镇中心”、“运河遗产”,以及后来的“线性文化遗产”和“环境”的出现,说明在结构遗产与管理遗产过程中,地缘—文化因素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5]。与其说遗产对象的边界更加明确了,倒不如说遗产对象本身的判定更加复杂了,而这个在逻辑上和《操作指南》等文献中提到的遗产边界也就更难界定了。就早期考古遗存而言,曾经使用过的名称非常之多,如“遗址”、“遗址群”、“墓葬”、“墓葬群”、“墓地”等,这表明同西方一直存在的问题一样[6],对于某一处考古遗存的存在方式和范围的判定,也一直是中国考古实践中的一个问题。界定某一处遗址属性的问题往往因为暴露不全面而遇到困难,这就使确定遗址或景观对象轮廓遇到了障碍。目前,考古学中出现的主要遗址分类,在基本材料层面上所关注的应该是如何使基本材料具有相对清晰的社会文化含义,根本的方法可能还在于强化对判断聚落形态和遗迹功能方面信息的搜集,否则,对于遗存的相对关系与组合功能就无法认知。但能够在大范围内对地层进行揭露并提取分布信息的考古项目往往是基本建设项目,由此,细化基本建设项目的物探、调查、信息提取与整理就成了当务之急。从文化景观的要素来说,不能给出地缘因素和人居模式间相互关系的考古学调查并不能算是完成了调查任务;而没有进行基本考古资源调查和保存压力认定的遗址规划与管理,应该被视为不合格的甚至具有破坏性的行为。景观考古学的基本调查方法可能会有助于进行综合性的信息搜集,也并不将研究视野局限在某一个发掘的遗址,因此也是目前在一定的地域内进行考古遗产资源调查的可行方法[7]。通常情况下,我国的遗产调查或者完全混同于文物普查,或者完全由考古调查取代,缺乏以地缘—文化景观为框架的专门遗产资源状况调查方法。文物普查重在“产量”,对于遗产对象的消失和破坏因素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8];考古调查则重在“分布”,对于遗产本身的实体状况无法给出明确的评估指标,两种调查对于“遗产对象”的具体处境都无法给出答案。因此,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在现有条件下建立一套以景观考古方法为依托的“地域—文化”遗产调查方法。
二 调研方法的基本内容和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巴拉宪章》(Burra Charter)将文化遗产价值作为一切围绕文化遗产而进行的保护和研究的根本依据,将“社会因素”与“社会需要”作为衡量遗产保护和管理方式的标准。将文化遗产保护实施过程划分为三个环节:文化遗产重要性评估(收集遗产对象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以及与同类进行比较;确定遗产对象最重要的价值项),确定保护的方案和策略(确定遗产对象所面临的压力),实施对该遗产的保护方案[9]。这里就牵扯到我们如何确定遗产对象的基本问题,即在进行遗产对象价值评估的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将遗产的内涵与实体对应起来。造成遗产对象界定不明的根本原因在于遗产对象在空间地域内的分布往往已经被完全颠覆或者揭露不完整[10]。另外,就遗产调查而言,我们认为它并不是单纯的价值汇总,相反,作为遗产资源调查,信息项的内容更多的应是围绕遗产实体本身的留存状态所设计[11]。遗产调查的基础依旧是实体调查、勘探以及测绘。在对遗产调查内容展开讨论前,我们希望能够将方法论证的切入点进行一定的解释,即对于遗产地理单元的定义。
1.遗产调查的地缘因素:土地使用模式与文化遗产的地理单元
究明遗产的地缘因素目标是确定遗产对象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目前在我国进行的相关调查主要是考古学调查[12],主要研究对象是一定地理区域(如盆地内小平原、河道流域谷地等)内某类别考古遗存的分布状况、规律以及演进方式。在调查过程中,被调查的遗产对象往往根据水源或者资源(如早期狩猎—采集时期对于食物来源的考虑以及农业耕作时期对于土地资源的考虑和青铜时代对于矿冶资源的考虑等)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分布特征。这说明,古代社会遗存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地理区域概念,即“土地使用模式”才是从根本上决定遗存分布与功能属性的因素,这也是景观考古学的基本态度。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古代城址和后期历史阶段的古代城市,由于遗产对象的功能不同,它们所利用的地缘因素也有较大差异[13]。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影响土地使用模式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生业经济形态、防御、行政、交通贸易、生产和人居环境模式之外,还有大量因素来自于意识形态传统领域或人的主观能动创造,在很多情景下,我们无法将土地结构模式单纯简化为“环境—适应”的基本格局,因为上述因素的复合作用可能才是结构遗产行为地域范围的限定条件。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划定遗产地域范围的决定因素并不在于理想的“完整性”,而在于现实的“复合性”。
遗产对象的地理单元除了上述几种之外,还可能出现跨地理区域的线性遗存,如大型防御工事、运河、文化传播路径等,因此,究明遗产对象所表现的土地使用模式、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所利用的地缘因素是认知遗产的首要任务[14]。我们认为,判定文化遗存所在地理单元结构的主要界定依据是,如某一类遗存相关环境及扩展范围足够对该遗存所见证的遗产行为赋予独立而完整的社会—文化含义,即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遗产地理单元。从构成上看,一般也就是按照功能派生出来的“遗存本体”、“功能背景”与“环境景观”;从内涵上看,这个地理空间范围就是遗产行为发生的整个区域。在遗产调查的实践过程中,遗产地理单元的轮廓在调查完全结束之后才可能清晰,对于这个单元的探索过程是与遗产调查相始终的。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遗产地缘的确定往往需要进行大面积的勘测调查,根本目的是为了明确勘测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模式沿革过程[15]。
遗产对象地理单元的大小取决于“遗产行为”的实质,遗产对象所在地缘界限的划定取决于对于该遗产对象所承载遗产行为的认识程度[16]。由于遗产存在形态的多种多样,我们必须在进行调查之前考虑几个最基本的问题:遗产对象所存在的文化地域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地域内围绕遗产发生的行为是什么?遗产行为与环境的关系是什么?很多情况下,城市和乡村背景相比具有更大的杂糅性。城市建设的需要往往使我们必须以某城市的文化遗产作为结构的单元对象,归根结底是一种以建设作为保护依据的方法,而遗产对象本身的文化地缘环境往往无法被深入细致地作为遗产对象的构成要素加以衡量。因此,我们需要首先从方法论上纠正遗产对象研究的入手角度问题。一个文化遗产研究客体只有在其所生存过的环境背景中才能有确切的定义,由此,我们希望能够将景观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借鉴到遗产研究中来。在具体操作上我们承认“系统论”还是最基本的视角,被我们“发现”的遗产行为的主体场所或者构造与环境构成了一个系统,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我们要定义的部分,对于遗产对象的实际管理步骤(认定、发掘、维护、评估、复原等)也就是系统关系“再物化”的过程[17]。在以往进行的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多数情况下,这个环节是被忽略的。这些环境因素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很多非物质的社会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讲,遗产地理单元调研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将遗产行为所发生的情境究明。无论采取怎样的数据收集手段,在遗产保护实践开始之前,遗产行为发生的地理空间都必须被明确界定。景观考古学在其中的作用不仅是认定所谓“系统范围”,更是明确不同遗存本身在过去社会背景中的具体含义、功能和社会角色。
2.确定遗产对象:文化遗产对象实体分布区域的认定、功能构成要素的分析
对于遗产对象本体的确认,主要是解决文化遗产实体曾经的存在方式问题,此阶段调查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对于遗产对象本体的界定工作。确定遗产的本体部分不是武断地划分保护区和非保护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于遗产对象本体功能结构的解剖过程,所谓区域的划分是在进行过缜密解剖之后自然出现的轮廓。首先是需要定义遗产行为构成要素,这个分析需要明确以下一些基本内容:遗产行为类别、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方式、物质载体、物质载体来源、物质载体含义,每一项内容都需要有明确的界定和对于内容的阐释。对于遗产对象本体的认知和地理单元的复合,基本上可以在实体层面上廓清遗产的社会属性。明确原始地缘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组织环境是遗产再物化的基础,原始地缘环境是指遗产对象在整个小地域范围内的分布方式,以及这些地形、地貌、资源分布模式等因素对于遗产对象形成、发展以及衰落的过程所起到的具体的作用[18]。
综上所述,对于某一地缘遗产对象的定义和状貌重构过程应该包括以下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应该都可以作为重要信息进行集成,并在搜集之初给予一定的性质判定:(1)遗产行为方面:遗产行为类别;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方式;物质载体;物质载体来源;物质载体含义;遗产行为的沿革过程。(2)遗产实体结构、地缘分布和环境:遗产实体结构留存状况;遗产结构功能分析;遗产对象的空间分布;遗产对象在环境地域中的布局和功能关系;遗产实体使用的沿革过程(与遗产行为的沿革过程相互补充)、使用后的废弃或其他形态的存在方式;在该遗产对象所依附的文化地域范围内,是否可以找到能够反映该遗产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底层堆积,这种堆积的内涵和连续性怎样。(3)综合信息分析:明确遗产对象的整体沿革过程、遗产行为与遗产对象分布的对应关系以及人地互动关系在景观塑造中的基本作用。
3.遗产社会—文化背景信息搜集与还原
遗产对象的背景信息基本就是围绕该遗产对象所发生的主要遗产行为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史背景信息,对于宗教遗产而言,这种文化信息背景的重要性自不必说,但更应当强调的是,思想背景或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较为典型的综合性研究是围绕古代四川地区盐业制造的考古学调研中对于摩崖造像和宗教材料的收集,这些资料明确了与生产遗存及宗教遗存之间的关系。这类背景遗存实体大致上有两种情况。即“独立于遗产对象之外”或者“存在于遗产对象中”的、与一定遗产行为相对应的社会背景遗迹。由于宗教行为在该地域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完全不同,导致了在一定地域内不同的分布和集中模式。对于自然宗教崇拜色彩较为浓重的地区,山川河流湖泊可能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它们与人居区域之间也有更为特殊的关系,如早期西欧与西北欧、原著民时代的澳洲和日本的情况。在对中国中古以来城市的考古中,宗教区域由于不同的原因往往被安排在不同的地点。又如欧洲中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教堂为中心的村镇格局。
除了反映遗产行为的思想与心理基础方面的信息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其他的相关信息放在其中,如对于地区文献历史的叙述等。重构社会—文化信息是必要的环节。一般而言,文献中获得的信息背景会更有利于对于遗产对象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对于文化遗产行为的解读。由于社会文化信息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我们在这里只把主要的几个线索提出来:(1)遗产行为主体文献背景追踪;(2)遗产对象与所依附地缘环境变迁的社会背景信息:不同阶段遗产对象和所附地域内社会变迁的文献信息反映、见诸考古手段揭露出的遗产对象存在时间内和地域内的社会信息;(3)遗产格局中的意识形态信息追踪:主要意识形态的物化表现,其思想史具体范畴是什么,这些物化形式能够反映出怎样的遗产行为动机,对遗产行为有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这种物化形式与遗产对象主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所共同构成的遗产格局具体是什么样的;(4)其他社会背景信息来源:如口述材料分析等。
4.遗产与现代社会关系(断裂分析)
一定地域—文化遗产对象现在生境的形成,在我国基本可以追溯到近现代化的阶段。这些社会存在的形式在长期的传统社会生境中存在着一个相对体系性的链条,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条划分为这样几个单元:遗产行为、遗产对象实体、社会条件、环境背景。在这里,对于地域—文化遗产的前几个方面的调查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对于遗产链条破裂的分析结论,这个分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判断在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某种社会均衡究竟是如何被打破的,以及这四个环节上究竟是哪些变化导致了链条的分解和最终实体的溶逝。在传统社会里,一定文化地域内的地表结构应该有着与现代条件下极不相同的状况,最主要的就是一定地域内的遗产构成要素之间具有与生俱来的组织性(如城市系统性的演进模式)。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对于“单体遗产对象”的破坏,相反,在近现代背景下出现的“破坏”基本上都是对于原有社会系统均衡性和组织性的彻底颠覆。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并不存在成熟的遗产保护意识[19],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破坏在当时并不是破坏,而往往是一种近乎合理的主流社会行为,也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拆毁行为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档案记录。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是遗产和遗产观念产生的重要时间段。我们认为对一个地域—文化遗产区域的全面调查,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遗产对象所在时代(至少传统社会中)的这种组织性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围绕组织性的断裂问题,需要进行调查的有以下一些方面:遗产行为结束的时间和原因(我们将这个时间认作是遗产存在链条断裂的起始点);遗产对象实体在遗产主体行为结束之后的处理方式(废弃过程、改造或者再利用);社会条件的变化对于链条破裂的作用过程及断裂对于当时当地社会的影响;断裂时期现代社会条件下地表环境结构的整体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和遗产实体以及遗产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过程;原有遗产生态的组织解体过程。对于遗产区域近现代土地使用演变以及破坏进行考察的重要性还没有被认识到[20]。
5.遗产的社会处境
我们认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由于将遗产和社群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对立,因此需要有一个比较宏观适用的调节机制来对遗产的社会生态进行必要的疏导和调节。目前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一般以建筑或者规划为主业,他们给出的很多规划方案并不能得到实施,根本原因在于“遗产”始终并没有被当作“社会存在”来看待,它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与现代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而目前的规划者对遗产利益相关的群体往往不够注意。保护的对象是谁的遗产?谁需要它们?在得到与失去之间有怎样的利害冲突?答案并不明确。
“遗产生境”包括两类状况:一类是遗产实体的物质环境状况,一类是遗产存在的现实社会氛围。对于实体环境的评估已经在国际上建立了一定的规范,而对于遗产现实社会生存境遇的调查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方法。目前对遗产部分的调查往往只局限于对于实体所遭受压力的来源调查,原因在于遗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等同于保护科学或者建筑规划学科,这使得遗产状况被简单地等同于实体保护环境评估。这种评估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对对象面临的全部生态进行了解和信息整合,更无法了解一定文化区域内由于组织系统遭受破坏而蕴含的威胁。事实上,近现代社会因素对于遗产链条的破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示范,即:源自于社会因素导致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的改变应被视为遗产保护最主要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遗产对象演进历程的始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将以下一些问题纳入“遗产生境”调查:遗产对象在近期与周边社会群体的相互关系;遗产利益相关群体都有哪些,以及利益相关的具体方式和程度;文化地域内社会群体的话语分析;近期针对遗产对象曾经进行过的任何形式的处理和动因;不同利益相关方目前所采取的态度是什么;目前围绕区域内遗产对象所出现的主要利益矛盾有哪些方面;现有的利益协调和管理方式是什么;利益协调之后对于遗产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如实体范围等;目前围绕遗产对象出现的相关政策和实施程度以及造成的影响;行政区划管理对遗产对象的文化性和地缘性的再结构;在现有的商业化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所扮演的角色和收益程度;利益相关方目前所受约束的来源,约束是否合理;对当地遗产“资源”开发的基本模式和政府行为角色;社会群体满意度调查;对于所调查地域—文化遗产近期核心事件的分析等。
三 结语
上述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在遗产对象的实体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生境中明确遗产对象的存在方式,它与现在遗产实践中使用的评估模式并不冲突。相反,我们认为,这个研究过程是进行任何遗产评估之前必须完成的数据积累,也是规划与保护方案提出的基础。遗产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遗产调查从一开始就必然是多学科合作的,但很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遗产规划实践中这种综合性调查的出现。本文所列举的需要考虑的因素虽难免挂一漏万,但它所包含的基本方面却是遗产保护行为实施之前必须进行调查的基本方向。原因在于,上述几方面内容决定了实施保护的对象内容,决定了遗产所面临威胁的环境、实体以及社会因素,更重要的是能够明确遗产的现实处境。由此,我们希望在对某一遗产的价值进行讨论之前,能够先行对这类遗产的存在方式进行切实的调查与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2]Cleere, H., ed. 1989.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Unwin Hyman.
[3]如美国建立的CRM(Cul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系统。
[4]De la Torre, Marta. 2001. Values and Site Management: New Case Studies.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Newsletter 16(2), 19-20.
[5]张杰、邓翔宇:《论聚落遗产与文化景观的系统保护》,《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8年第1卷第3期。
[6]Hodder, I. 2001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文化遗产中的基本地域区划方式一直争论颇多。我国现在考古和遗产领域中经常出现的主要划分单位有:遗存(cultural remains)、遗迹(archaeological features)、遗址(archaeological site)、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等。这些概念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界定并不明确。我们不主张对于“遗址”概念进行无休止的追究,也并不打算将这些概念做定性或者量化分析,因为“遗址”的界限往往在实践中无法明确解说。作为考古遗产资源调查的主要方法,景观法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人类对该片土地的使用方式,在使用阶段该结构与周边同时期结构及资源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调查阶段能够反映该结构功能的实体部分的留存状况。因此,它并不特别强调对于遗址本身划定明确的界限,而更加看重在一定地理单元范围内能够根据人地互动关系解释的“整体性事实”以及地缘因素在塑造遗产形态中所起的作用。而这对于整个地域内遗产的展示与阐释都非常重要。对于文化景观整体性的重构可参考Jean Paul Le Bihan对于韦桑岛古代宗教遗存的景观考古学研究以及John Rick对于Chavín de Huántar宗教文化景观人地互动关系的调查。
[8]相关材料可见于各地文物普查登记表格的登记项设置。
[9]详见Australia ICOMOS 1988。
[10]遗产对象边界的划定是遗产调查最基本的任务之一。直接决定边界划定的因素有三个:遗产对象包含的内容;能够采用的边界调查手段;文化背景随着地理环境变迁而使遗产对象出现的意义失落。
[11]B.A. Kipfer, 2008, The Archaeologist's Fieldwork Companion, Blackwell. Darvill, T. and Fulton, A.K. 1998. The Monuments at Risk Survey of England 1995. Bournemouth University and English Heritage.
[12]对于早期聚落的地域分布特征研究参见陈星灿、刘莉、李润权、华翰维、艾琳:《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第161~218页;对于某一工业遗产地域分布特征参见李水城、罗泰:《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中国盐业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关于人居的地缘模式可参见徐良高:《“人居环境”课题预研究·三代时期》(未发表),2008年;关于城址分布、结构与保存状况另见杭侃:《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城址类型及其所反映的问题》,《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13]越是早期的遗产分布,其地缘因素所占的主导地位越明显;而晚期的如运河城市带等城市遗存除了地缘因素之外,人迹在景观中所占据的比例会相应地提高,而这些因素往往也正是遗产分析所无法回避的最重要的部分。遗产对象的空间分布有着非常大的伸缩性。从整体遗产对象保护的角度而言,最大的遗产对象可以认为是“城市带”或者“线性遗产”,如运河、文化途径等(参见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te Convention)。从这一角度讲,遗产的区域分布就是遗产本质的外观体现。目前主要采取的调查方法包括物探、钻探、地表采集、试掘、区系调查以及卫片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遗产实际的地理单位很可能要超出实体在图像上所反映出来的范围,这恰恰是文化外延性的重要体现。
[14]张杰与邓翔宇对于中国目前以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建立的遗产保护体系进行过较详细的评述。该文章表明,目前城市规划行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考古方法的重要价值和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柱性意义以及地缘环境因素的意义。文章认为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可以成为规划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目前的多级保护体系存在的较大问题是使用行政区划概念指导遗产实践;而考古学对于规划的本质作用并不仅局限于提供系统或者分布,而是在土地使用模式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保存的对象以及对象存在的基本方式。文章作者反复使用山水环境的概念,实际上在景观考古学框架内对于环境已经有明确的定义。这种环境的定义并非是围绕在人居周围的山水地形,而是一切该地域内古人活动的背景。景观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并不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强调研究人地互动关系和土地使用模式。由此定义的遗产环境才具有认知上的意义。而从景观考古学角度出发对于地域及其遗产的界定才有可能完成对遗产的全面认识,由此,我们认为所有遗产规划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对于地缘因素以及人地互动模式的认知,这个认知只有通过景观考古学的遗产调研行为来实现,否则就只能将一地的遗产格局塑造成规划者“想要”的形态,从而彻底颠覆遗产的“原真性”。遗憾的是,我们尚且不知道目前国内进行的遗产规划究竟有多少进行过全面的遗产资源调查。在该文章中,作者从系统论与结构论的视角来对遗产规划进行类比,但对于考古学而言,结构论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只“做形式结构比较而不问意义内容”。这也是中国目前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严重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目前的文化遗产保护角度过于单一,考古学所应起到的基石作用并未被规划者意识到。(参见张杰、邓翔宇:《论聚落遗产与文化景观的系统保护》,《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8年第1卷第3期;关于结构论的考古学批判可参见Hodder, I. 2001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 rchaeolog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即资源清单调查。调查者应该给出一份项目地域内的文化资源的报告,内容包括环境背景、该地域内已知的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以及对相关文献信息的描述。通过物探、铲探等方法得出分布的范围和深度。调查区域必须明确标注在地图上,明确主要的遗产对象与环境的相对关系和文化来源,确定遗产行为发生的地缘范围。根据调查结果,报告者即可以对此地域的研究价值进行评估,也就是该地域出现未经扰动的考古堆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并由此提出管理的建议。
[16]较为特殊的一类遗产对象是具有明显自然属性的宗教文化景观遗产,这种遗产在亚洲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中国、日本及澳洲等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长江上游地区以盐业生产为中心分布的宗教石刻造像遗存、日本奈良若草山宗教自然遗存、大西洋韦桑岛潮汐宗教景观以及被澳洲人认为是宗教神域的圣山等。
[17]较大规模的这类重构(也是最为极端的案例)如日本佐贺县吉野里聚落公园的做法一直还处于争议之中。
[18]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某地遗产资源整体性的破坏过程需要特别加以注意。因为这种变化很可能暗示着一种遗产行为与环境平衡关系的断裂。我们很难完整构拟出一个遗产对象的溶逝过程,整体格局的瓦解过程往往是长时间内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变迁因素所导致的,而这种发生在地理面貌或者建筑群落的变迁过程往往无法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文献资料得出确切的结论。目前,对地缘遗产对象实体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遗址形成过程分析;其二是通过航拍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实现对于古代遗址遗迹空间分布的构拟。这两种分析的必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遗产对象的实体分布状况进行量化。遗产对象本身实体的变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遗产行为者的需求及其与上述三个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遗产对象、遗产行为以及遗产环境三方面的相互关联,我们有可能将一定地缘条件中的某个遗产对象进行确切的定义并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
[19]只有出现了留存的需要,才有所谓遗产的出现,这种行为的大规模出现颠覆了各个地区对于古代社会遗存的基本处理形态。
[20]多数情况下对于地域—文化遗产的调查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缺失,原因实际上是对于遗产对象本身的衍生过程阶段划分不明确。对于遗产链条断裂的过程往往只能停留在遗产实体的病理分析上,即只能够从纯粹的理化过程进行自然损坏原理的分析,而对于遗产对象变化的社会动因往往并不重视。换言之,保护研究被简化到了实体操作技术层面。这种单纯意义上的保护研究策略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保护科学与社会研究之间的严重脱节。事实上,对于整个地域—文化遗产的链条断裂过程我们往往并不清楚,而如果对于地域—文化遗产对象的界定再不明确,那么保护的对象就更可质疑。
来源:《东南文化》2009年4期第20~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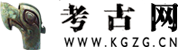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